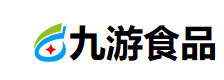近日,上海网红日料品牌小锄匠寿喜烧(以下简称“小锄匠”)关闭所有门店引发关注。
据餐饮见闻了解,近两年来,不论是平价日料店还是高价日料店,有多个知名品牌因经营困难而倒闭。
例如曾被誉为“上海日料天花板”的赤坂亭;杭州老牌网红日料品牌山葵家;平价里的知名品牌一口组·平价日料屋皆在去年接连关店。
头部品牌纷纷倒闭,如赤坂亭曾被誉为“上海日料天花板”,人均消费超300元,巅峰期全国门店超40家,但2024年多地门店关闭,并陷入欠薪、抵押资产等负面风波。
山葵家作为杭州老牌日料品牌,因资金链断裂和扩张过快,2024年9月关闭所有直营店。
小锄匠寿喜烧凭借“富士山寿喜烧”走红,但2025年2月因经营困境关闭所有门店,仅剩福州独立运营店。
其他高端日料品牌如上海“鮨心和”、北京“鮨·泽 Omakase”、杭州“万岛日本料理”等也相继闭店。
行业整体萎缩明显,2023年8月至2024年8月,国内日料店数量从52,276家锐减至28,631家,超2万家倒闭,近乎一半的日料品牌退出市场。
过去两年,北京、上海、深圳三城合计关闭了82家高端日料店,关店率34%,远高于中餐(26%)及西餐(22%)。
消费降级是重要因素之一,经济下行压力下,消费者更倾向于平价餐饮,2024年日料人均消费100元以下门店占比升至69%(2022年为54%)。
核污水事件对日料行业冲击巨大,2023年日本核污水排海后,消费者对海鲜类日料的恐慌加剧,高端日料因依赖日本食材陷入信任危机,客流量骤降50%以上。
此外,高端日料成本高企(食材、租金、人工),扩张过快导致资金链断裂,本土平价品牌挤压市场空间,也是导致这些日料店倒闭的重要原因。
自日本水产禁令后,尽管部分品牌改用挪威、加拿大等替代食材,但消费者对“日料=日本海鲜”的固有认知难以扭转,海鲜类日料的食品安全焦虑持续存在,毕竟日料俩字中的这个“日”也改变不了。
同时,高端日料的核心竞争力(如蓝鳍金枪鱼、北海道海胆)依然依赖日本原产地,替代食材难以复刻品质,这也导致客单价和口碑双降。
另外还有消费市场的变化。数据显示,2024年,日料客单价普遍下调30%-50%,如上海“洵 sushi”从1380元降至400元,但仍难挽回流失的中高端客群。
平价日料(如鲜目录、池田寿司)及本土火锅品牌(如海鲜集市火锅)以高性价比抢占市场,挤压了传统日料的生存空间。
此外,滨寿司、寿司郎、KURA寿司等平价连锁回转寿司品牌纷纷在中国市场扩张,其寿司价格集中在10元至20元区间,凭借高性价比和新颖的经营模式吸引了大量消费者。
值得一提的是,寿司郎、藏寿司等平价连锁品牌加速扩张,这也加剧了本土日料的内卷。例如寿司郎计划2026年中国门店达201家。
另外,高端日料过度依赖“仪式感营销”(如Omakase),忽视菜品创新,导致消费者审美疲劳。日料行业缺乏创新,同质化严重,也成为品类发展的痛点。
面对如今市场低迷的困境,一些日料品牌也在积极想办法,力求在“夹缝”中发展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。
一些品牌将人均消费控制在50-100元区间,推出低价套餐(如9.8元鱼生饭)吸引大众客群。
例如,N多寿司和鲜目录寿司等品牌通过平价策略和外卖模式,成功吸引了大量消费者。此外,简餐化的日料店进一步降低了人均消费价格,使得日料更加亲民。
一些品牌明确标注非日本来源食材(如挪威三文鱼、国产海胆),强化供应链透明度。同时,引入中式寿司、亚洲锅物(如冬阴功锅、椰浆鸡锅),弱化“纯日式”标签。
这种本土化策略不仅缓解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担忧,还拓展了品牌的市场边界。
例如,一些日料品牌通过社交媒体推广特色菜品,成功吸引了大量年轻消费者,提升了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。
与国内养殖基地合作,降低食材成本(如国产三文鱼价格仅为进口的1/3)。部分品牌通过缩减门店面积、优化人工配置,实现降本增效。
例如,一些日料品牌通过优化供应链,减少了对进口食材的依赖,降低了成本,同时通过调整门店布局和人员配置,提高了运营效率。
目前,不少综合日料大店会提供全品类的日料,包括炸物、拉面、寿司、刺身等等。虽然能够满足消费者多元的需求,但却对品牌食材采购、管理、供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,导致大店的成本较高,连锁化发展有难度。综合日料品牌要提升效率,可从降低SKU入手。
降低SKU,并不等同于做拉面馆、寿司店等单品类店,而是在日料全品类中挑选数个品类,把SKU调整至适宜的量。
小编认为,日料品类的危机既是行业洗牌的阵痛,也可以说是是转型升级的契机。
核污水事件加速了市场分化,消费降级倒逼品牌回归性价比本质,而本土化与创新则为幸存者开辟新赛道。